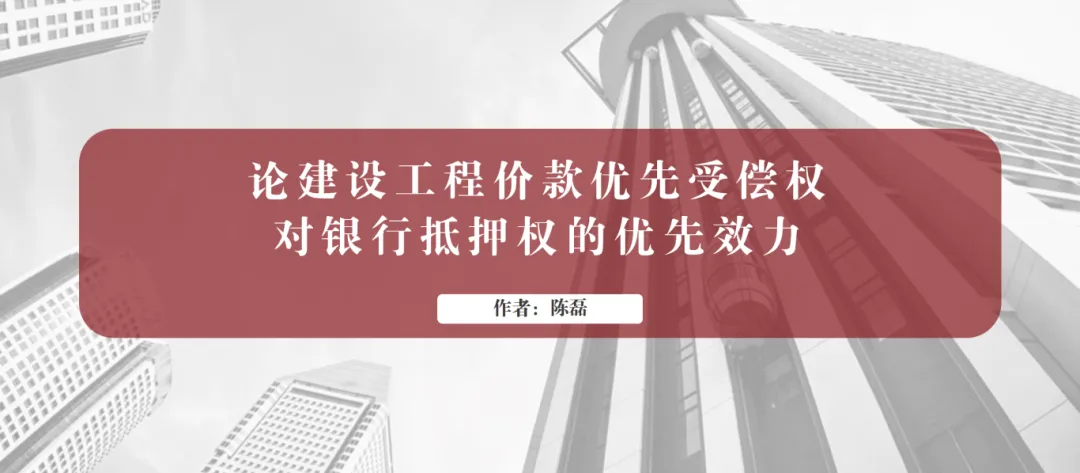
在建设工程领域,发包人以在建工程设定抵押获取融资、承包人因工程款拖欠主张优先受偿的权利冲突已成常态。银行抵押权虽以登记为公示方式具备物权效力,但法律明确赋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以下简称"工程款优先权")更优的清偿顺位。这种优先性并非立法随意创设,而是基于在建工程的特殊属性、法律价值的优先选择及司法实践的长期验证形成的制度共识。本文结合法律规定、法理基础与司法实践,系统论证工程款优先权优于银行抵押权的正当性与必然性。
工程款优先权对银行抵押权的优先效力,首先源于在建工程的本质特征与法律价值的层级判断,构成制度存在的法理基石。
(一)在建工程的特殊属性决定权利优先顺位。
在建工程作为"成长中"的不动产,与已完成物权登记的成熟不动产存在本质区别,其特殊性直接影响权利配置逻辑:
1. 权利客体的依赖性:在建工程的价值形成与状态定型完全依赖承包人的劳动投入,从施工材料的物化到工程结构的搭建,承包人的专业劳动是抵押物价值的核心来源。银行抵押权的实现以工程价值存在为前提,而该价值的创造者理应获得优先清偿的权利,这符合"贡献者优先"的民法公平原则。
2. 物权状态的未完成性:在建工程尚未完成法定物权登记,其权属状态与价值范围均处于不确定状态。银行在接受在建工程抵押时,明知其物权公示不完整的风险,却仍选择提供融资,应自行承担权利实现时的顺位劣后后果。正如实务观点所指出,金融机构设定抵押时本就负有核查工程事实状态与价款结算情况的义务。
3. 权利产生的同步性:工程款债权与在建工程的价值增长同步发生,而银行抵押权通常是工程建设过程中后置设立的担保权利。从权利发生时序看,承包人的劳动贡献先于抵押权设立,优先保护在先形成的权利符合权利实现的一般逻辑。
(二)生存权优先于财产权的价值取舍。
工程款优先权的核心内容包含建筑工人的劳动报酬,而劳动报酬债权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益。在法律价值体系中,生存权作为基本人权,具有优先于商业性财产权的天然位阶:
1.银行抵押权所保障的是金融机构的商业信贷利益,属于典型的财产权范畴;而工程款优先权中蕴含的工人工资请求权,承载着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共利益属性。正如崔建远教授所指出,工程款优先权的立法政策核心在于确保包含工人工资的工程价款优先实现。
2.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明确,承包人放弃优先权的行为若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则归于无效,这一规则从反面印证了生存权保护在优先权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当银行抵押权与工程款优先权冲突时,优先保护后者本质上是公共利益对商业利益的合理优先。
我国法律体系通过层级化的规范设置,明确确立了工程款优先权优于银行抵押权的规则,形成了从基本法律到司法解释的完整依据链条。
(一)法律层面的直接规定与衔接
1.《民法典》的传承与明确:《民法典》第807条承继原《合同法》第286条的核心内容,明确承包人就工程折价或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这一规定未附加登记等生效条件,属于法定权利的直接赋予,其效力不依赖于当事人约定或权利公示。
2. 担保物权规则的例外兼容:《民法典》第386条(原《物权法》第170条)规定担保物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但设置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但书条款。工程款优先权即属于该但书所指的法定例外情形,其优先于抵押权的效力获得担保物权一般规则的认可。
(二)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的强化适用
1. 优先权顺位的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首次明确"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这一规则被2020年《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36条延续,形成了司法实践的一贯立场。
2. 司法裁判的实践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最高法民终233号案件中明确指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相较于抵押权具有相对优先的清偿顺位,即使承包人部分放弃优先权,其剩余权利仍优先于其他抵押权人。这一裁判要旨进一步巩固了优先权的优先地位。
3. 权利范围的清晰界定:司法解释明确工程款优先权的范围包括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费用,甚至包含合法利润,而银行抵押权的担保范围通常限于贷款本息,从权利内容看,优先权保障的核心利益更具优先保护的必要性。
司法实践通过细化优先权的行使标准、明确金融机构的注意义务,构建了优先权与抵押权冲突的合理解决机制,印证了优先权优先的实践可行性。
(一)优先权行使的规范化消解权利冲突风险法律与司法解释通过明确优先权的行使要件,避免了权利滥用对抵押权人造成的不当损害:
1. 主体范围的限定:优先权主体限于施工合同承包人、合法分包的实际施工人及装饰装修工程承包人等直接贡献劳动的主体,勘察设计人等非核心施工主体通常不享有优先权,防止权利主体的不当扩张。
2. 行使期限的规制:优先权行使期限为六个月,自工程竣工或约定竣工之日起算,未竣工工程自合同解除之日起算,这一除斥期间的设置为抵押权人提供了可预期的权利行使窗口期。
3. 受偿范围的边界:优先权仅对承包人实际投入形成的工程价值优先受偿,垫资款中未物化为工程的部分、违约金等损失均不纳入优先范围,避免了对抵押权实现范围的过度挤压。
(二)金融机构的风险防控义务匹配优先权效力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接受在建工程抵押时负有法定的审慎注意义务,其风险防控能力足以应对优先权带来的不确定性:
1. 事前核查义务:金融机构在设定抵押前,应当核查工程的施工进度、价款结算情况及承包人的付款请求权状态,通过要求发包人提供工程款支付证明、预留价款保证金等方式防范风险。这一义务在《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中已有明确要求。
2. 合同约定防控:银行可在抵押合同中约定发包人需将贷款专项用于工程建设、定期披露工程款支付情况,并赋予抵押权人在发包人拖欠工程款时的救济权利。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实践也认可,承包人与抵押权人达成的合理顺位约定在不损害工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效。
3. 登记公示补充:部分地区已试点工程款优先权登记制度,金融机构可通过查询登记信息掌握优先权存续情况,未来随着统一登记制度的建立,优先权的隐蔽性问题将进一步得到解决。
(三)司法实践中的权利平衡机制法院在审理权利冲突案件时,通过精细化裁判实现优先权与抵押权的利益平衡:
1.部分优先规则:在承包人仅对部分工程享有优先权或放弃部分优先权的情况下,银行抵押权可在未受优先权覆盖的工程范围内优先实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发布的案例中,认定承包人对108套房产放弃优先权的行为有效,但对其余95.5%的工程仍享有优先受偿权。
2.价值区分规则:对于装饰装修工程,承包人仅在工程增加价值的范围内优先受偿,不影响建筑物原有价值上抵押权的实现,形成了权利行使的空间边界。
3.过错归责规则:若承包人与发包人恶意串通虚增工程款或转移工程价值,法院可否定虚假部分的优先受偿权,保护抵押权人的善意信赖利益。
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实践普遍承认建设工程相关优先权对抵押权的优先效力,形成了具有共性的制度选择,为我国制度提供了参照。法国民法将建设工程优先权归类为"不动产特别优先权",明确规定工匠、承揽人对其建造的建筑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其效力优先于抵押权,且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仅需通过扣押建筑物的方式行使权利。日本民法中的"先取特权"制度同样赋予建筑业者对其承建的建筑物以优先受偿权,在清偿顺位上明确优先于一般抵押权,其立法理由同样在于保护劳动者报酬与工程投入的特殊价值。 这些国家的制度设计表明,赋予建设工程相关优先权优先于抵押权的效力,是应对建筑业特点、平衡各方利益的共同选择,我国的制度设置与国际立法通例具有一致性。
结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银行抵押权的效力,并非简单的法律特殊规定,而是法理逻辑、立法价值与实践需求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从法理层面看,在建工程的劳动依赖性与生存权保障的优先性构成了权利优先的本质依据;从法律层面讲,《民法典》及司法解释形成了明确的优先性规范体系;从实践层面看,优先权行使的规范化与金融机构的风险防控能力实现了利益平衡。这一制度安排既保障了建筑工人的基本权益,维护了建筑业的健康发展,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可操作的风险防控路径。在权利冲突解决中坚持工程款优先权优先的规则,既是对法律规定的严格遵循,也是对社会公平与行业现实的充分回应。
*本文所有观点均为律师个人观点,不代表律所立场,仅供参考。